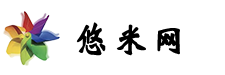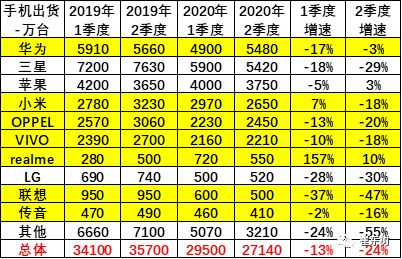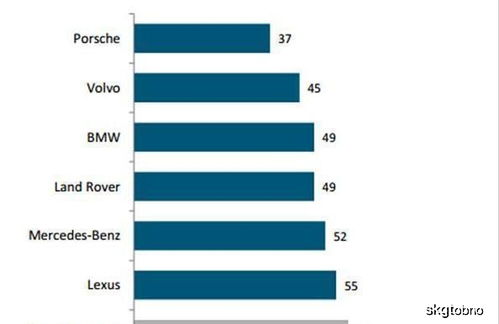许多女性出生起便被无形的“茧”包裹着:生活中无处不在的“糖衣陷阱”、“浪漫爱诱惑”、贫穷……无形中限制了女性的发展并给女性带来很多困扰。面对这些问题,女性该如何“破茧”,从而追寻到更好的自己?
钛媒体《正经知识研究站》第7期邀请到予她同行公益基金发起人 梁钰@梁钰stacey,和大家深入聊聊女性破茧之路。
直播回放地址:https://video.weibo.com/show?fid=1042211:4877850000687193
本期嘉宾:予她同行公益基金发起人 梁钰
主持人:女性有哪些生来就围绕在身边的[茧](身为女性有哪些无形的束缚)
梁钰:我觉得其实它的束缚是挺多的,很多它并不是我们自己的主观,或者我们自己靠努力就能够去改变的。我觉得对于女孩子来说最重要的事情是你可能去改变的,就是从自己的家庭去改变,更多的是原生家庭。就比如像宅基地,宅基地中登记了为女性的只有20%,房产中有多少又是女性?其实有更多的。我觉得这个事情还是属于自己的原生家庭方面。
主持人:波伏娃曾写道:“男人的极大幸运在于,他不论在成年还是在小时候,必须踏上一条极为艰苦的道路,不过这是一条最可靠的道路;女人的不幸则在于被几乎不可抗拒的诱惑包围着;她不被要求奋发向上只被鼓励滑下去到达极乐。”你如何看待女性被教导应该“柔弱”、可以“享受” ?当女性被这种声音包围,该如何保持坚定?
梁钰:我觉得波伏娃老师讲这个话,说的是一个意识,是一个文化层面上的。整个社会上,可能从思想上就这么去说:“男性天生他可能走这样一条比较艰苦的道路”。但是我们如果从实际层面上来考虑这个事情,其实女性才是生下来注定要走上一条非常艰辛的道路,女性其实一辈子都在出走,从原生家庭里出走,从原本的不断的各个的你的熟悉的圈层里面不断地出走。我们很难去拥有一个自己的固定的资产、圈层。它其实在我们没有这样一个非常客观、有形的东西的前提条件下,在我们没有一个自己的资产、没有一个自己的空间的前提条件下。其实内心你再怎么去改变、给自己打气,其实都是很后面的事情。
就像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我们首先要完成自己最初级的生理的需求。对于大多数的女孩子来说最重要的事情是能够通过各种方式去累积属于自己的一个资产,它在自己的名下、要有法律认可。我知道有很多的女性,她可能她不太了解法律,她可能会觉得她通过找到一个有房子的伴侣,她就成了一个有自己资产,有自己的空间的人。但是现实情况它不是这样的,我所以我觉得对于女性来,最重要的是要通过自己的努力劳动去构建自己的资产,自己的生活圈子。
主持人:从小到大以女性为目标群体的书籍,影视,音乐等等作品似乎都离不开“爱情”,反观男性向作品,“爱情”没那么重要,更像是一种可收集的“象征物”。您是怎么看待浪漫爱的?你认为什么是浪漫爱?
梁钰:我在思考爱情是不是被社会所建构出来的?因为,这个东西只有女的在追寻。当一个东西它只有女的在追寻的时候,我就会打上一个警惕。所以我一直在思考,我没有一个答案。我对这件事情我一直在想,爱情到底是什么?亲密关系到底是什么?我们寻求的到底是什么?如果我们寻求的是一个可以说话的人,或者可以深度沟通的人。但据我的观察,你不论是我们年龄层,还是我妈妈年龄层,甚至是再上一个年龄层,我们自己想一想,你说话的人到了最后都是你的姐妹。
首先我觉得,“爱情”更多是被建构的,人其实是一个群居动物。我们需要跟家庭,也就是你的亲缘关系以及朋友之间、和友邻建立关系。在这么多的文化中,所有人都是这样子生活的,它就构成了一个非常稳健的社会形态,它就是一个主流的社会形态,它往往会和你的生活要挂钩的。比如你有没有一个非常完美符合社会标准定义的伴侣。其实在各种的社会的大环境下,它会给你构建出了这样的一个目标,其实就像打游戏一样。它为了让你达成目标,不管是从社会稳定性的建构也好,不断地发出各种各样的任务对游戏进行构建。所以大家就会想着我要去完成,去寻找一个很好伴侣的游戏任务。会通过不断的影视作品去美化它。
我可能会不太清楚浪漫的爱情它到底是否真切的存在。我觉得它可能是存在的。但是就算是存在,我觉得浪漫的爱情和亲密关系它并不是划等号。可能浪漫的爱情它是那么短暂的一段时间,或者你并不一定会跟你有特别浪漫爱情的人构建很长久的亲密关系。我是这么看。
主持人:对“浪漫爱”的憧憬已经无形中印在许多人潜意识中,你认为应该如何看待这件事?
梁钰:我觉得问题不大,人一辈子想要追寻的事情很多,也不只有浪漫爱情这件事情。最重要的事情就是人要去感受自己的身体和内心。我觉得女人其实生活更多的时候可以靠直觉,不要去想那么多,要真心地相信自己的感受。人活着是为了啥?就是为了让自己开心跟舒服。如果当下的生活是很开心、舒服的,那就没有问题。如果当下的生活不开心、不舒服了,那我们就要诚实且真诚地找出问题的缘由。
有的女性朋友。她不开心不舒服,可能是因为她的工作真的很辛苦,升职也非常的困难。她就觉得解决方法是去找一个有房的男的,这样她就可以节省掉租房的成本,这样她就能开心了。这个事情就跟拆东墙补西墙的逻辑是差不多的。
如果想解决你的问题,就得从这个问题的本身去解决,而不是只是找一个别的方法,看上去能解决,但其实并不能解决的。诚实地面对自己的感受,针对问题找出真正的解决方案。
主持人:日本女性学、性别研究领域的开拓者上野千鹤子老师曾建议女性“不要糊弄自己”,你认为当代女性有哪些常见的“自我糊弄”?女性又该如何“看见”自己的需求、能力等?
梁钰:首先我对上野老师的“自我糊弄”先解释一下,在当时那个语境下,它是一个非常严厉的指责,而不是对年轻女性的“建议”。
关于年轻女性在生活中糊弄自己。跟我们时代的发展是有关系的。毕竟我们女人进入社会劳动的时间真的不是特别长,意思就是我们还没有传承,构成一个代际的传承,这是我自己的一个感受。整个社会上女孩子对女性、对于自己的持续的职场的发展,或者持续的职场要往前一步的思想思浪潮并没有很强大。很多人总是会觉得我现在这样也很好,没关系,我可以退一步休息一下,或者我现在想不明白也没关系,我过几年再想一想也是一样的,我感觉很多女孩子她并没有规划自己人生的想法,觉得真的觉得自己到了什么年纪,她自然而然就是什么样的。当然不是。人生都是靠自己争取来的。对,我觉得大家真的不要糊弄自己,人生真的是要去争取。
主持人:你认为现代的“信息茧房”是否也会成为女性发展的一层“茧”呢?该如何应对?
梁钰:我觉得信息茧房,它对于所有人都会是发展的一个茧的。对于女性当然是一样的,如何去破,你就只能去看各种各样的信息。而且我觉得最重要的事情是要保持一个非常open的态度,去接纳不同的信息。它有很多的信息,它可能只是不迎合我们的喜好,要保持着一种学习的心态。它跟我不一样,但是我还是很想学习一下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东西。也不要急着去抵触,急着去抨击。有一个新的东西出来,很多的人他会出于恐惧去攻击他的,这是非常正常的。对于自己不了解的知识信息,所以对我们自己来说更重要的事情,秉着一种开放的态度不断地去学习,去了解,这样才能够不被这个时代落下。你逃避也是没有用的,逃避还是会发展的。
主持人:您自身有没有一些破茧的经历,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吗?
梁钰:首先我觉得每一个人的经历都是独一无二的,最重要的就是遵循自己的内心,自己的感受,你开心就是开心,不开心就是不开心。
我想分享的是把自己的身体想象成你的大猫咪,就是你最爱的大猫咪就是我们自己,只是我们只有我们的灵魂,我们的大脑在操控我们这只大猫咪。大猫咪往哪走、吃什么、干什么,都是受你操控的。所以你要好好地照顾你自己的这只大猫咪,不能去虐待它,你要好好地去照顾它的身体的每一寸感受。所以我就是这么对我自己的。
破茧这个事情,在这条的道路上,它会有很多的阻碍,我觉得更重要的就是你要听从自己的声音,要树立一个很坚定的目标。我觉得我破茧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我知道我自己想要什么。我的破茧离开了很多人,我在这一路上可能离开了很多我的朋友、亲戚,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要坚定自己的目标,因为人生真的没有人可以去替自己承受任何的东西。
主持人:聊到破茧和行动,我观察到[予她同行]很多行动都和“月经”相关,最初为何会选择这个方向?
梁钰:最开始的时候在湖北疫情的时候,帮助女生医护捐助安心裤,因为首先那个时候大家都在捐口罩、捐防护服,你自然就会想着还有点什么别的大家没想到的地方。其实对于女的来说,当时我看到她们穿防护服要穿十几二十个小时,很自然地就会想到她来月经怎么办?大家有需求,从那个时候就开始一点一点去做这个事情。
主持人:近期网络又开始热议“月经羞耻”相关话题,你认为为什么正常的生理现象会变成“月经羞耻”,又该如何破除月经羞耻?
梁钰:第一层,大家对于生理知识并不了解,它是随着改革80年代开放才进入的中国。在最开始的时候,卫生巾它是一个奢侈品,它是摆在百货大楼里头卖的,你要拿特供的票去买的舶来品。在我妈妈他说他90年代的时候,她用的还是草纸。大家确实对这件事情她的认知并不清楚,大家的科普并不广泛,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所以就要大家不断地去说,一而再,再而三地去说。我觉得语言是有力量的。在2020年的时候,刚开始做这个事情,还是觉得很敏感的。那个时候月经不让说,卫生巾不让说。随着大家更多的社会的讨论,更多的人进行科普,慢慢地这几年才开始讨论。
第二层原因,确实是有非常多的人、文化、宗教。它会通过月经来污名化女性。月经只是用他们用来污名化女性和羞辱女性的一个手段而已。它其实就跟“妇女”一样,“妇女”这个词汇,它其实就是一个非常普通的词汇,但是在这几年之前是用来骂人的,用来羞辱女性的。文化还是要进一步的发展,但是我相信这个社会、世界,还是会通过每一个人的努力而改变的。
主持人:[予她同行]关注到了“月经贫困”,那除了给山区女孩们发放卫生巾这些实际物资外,是否还会做些思想层面的帮助呢?
梁钰:我们是国内唯一一家每个月都要会发卫生巾的公益项目。我们还会下乡去给她们讲生理知识讲座,告诉她人体的构造之类。我们会中间会抽20分钟,有一个叫夸夸课堂,我们会鼓励她去夸自己,一定要佐证故事。我们会希望她们去跟对方说出自己的爱意,我觉得很动人。我们给她们的卫生巾,每个月会有每个人有一个盒子,盒子的外面我们会做一些设计,都会尽量避免那种特别幼态、弱态。我们会尽量地用一种我们是在支持你们,用比较有力量的这种感觉。我们每次下乡的时候,我们都会招募一些助教,比如之前有一些有艺人,有像徐娇,之前有跟我们一起下乡,还会有一些博主,有一些企业家、艺术家等等。
我想讲的卫生巾贫困,它其实非常严重,非常普遍的一个事情,我们其实没有办法去判断到底是真正的因为经济的贫困,还是女性的贫困。我觉得扶贫其实从某种意义上做得其实还是挺好的。针对家庭的扶贫都是比较强硬的,有在做的。但是现在独生女时代已经过去了,所以一个家庭里面她算上母亲,她可能来月经的可能一般会有3- 4位女性,你如果一个月的卫生巾的,一个月如果25块,其实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开销,所以我们所知道的有很多的女孩子,她可能真的用袜子或者用布条,或者用草纸,或者她可能真的用那种很劣质的10块钱一大包的那种。她可能舍不得换,一片用两天整个裤子上都是血。它其实是一个非常广泛的事情,所以咋办对吧?只能希望是能帮一个女孩是一个女孩,要让她知道你本可以不用这样,毕竟这也不是买个包对吧。她是可以通过自己学习努力出来,出来你找一个工作,你是可以用上好的卫生巾,你是可以有尊严地生活的,因为那些地方有很多女性,她哪怕他自己赚了钱,她也舍不得对自己好一点。其实我们也是希望传递一个你可以,你值得好好生活的理念。
主持人:山区女孩的声音可能较难传达出来,除了月经困境外,还有哪些问题需要大家关注?
梁钰:我们前段时间收到一个小妹妹的发给老师的消息,“老师我就不读书了,爸妈都在外面打工,家里还有弟弟妹妹,奶奶也身体不好,我也没有办法。我会在网上购买一些学习资料,自己能学一点是一点,就真的很对不起老师,我没有办法再学习了”。其实很多我觉得非常多,尤其是女性,更容易陷入贫困。底层的小女孩,真的是底层中的底层。女孩子连卫生巾都没有,她的人生中还能拥有什么?有非常多问题,我觉得其实对于大家来说,不只是山区里的小女孩需要大家的关注和帮助,其实很简单,就从身边的小女孩,身边的女性做起对吧。
主持人:您接受采访时曾讲到山区那些女孩见到“活得理工科女博士”很兴奋,意识到了“女性力量”“女性榜样”的力量。你认为什么程度可以成为女孩们的榜样,又该如何将力量传达给女孩们呢?
梁钰:我其实我的感受,每个人都是有自己的优点的,不是我一定要做到什么程度,我才能成为别人的榜样。我觉得我们每一个女的都可以成为榜样,每一个女生她都可以帮助别人。首先最重要照顾好自己,这是最重要的。这个世界上每一个女的生存多困难,真的是照顾好自己是最重要的。第二就是可能力所能及可以帮一帮其他的女性,不能帮的也不要强求。不要一天到晚想着去帮别人,这也是很重要的。
我们团队有一个小女孩,大学刚毕业,我们劝她刚毕业可以去外面走一走,她就去了深圳,工资就翻了很多,发了很多钱。她就觉得世界还能这样。有一天她在楼下便利店发现两个小女孩觉得人不对劲,去跟人家小女孩聊天,小女孩只有16岁,在当地读初中,被人性侵了辍学回来打工,我们帮她们找了一些心理的介入机构以及一些有钱的姐姐们,支持她们继续读书。
但这个事情是很触动到我的。第一,那个女孩子先照顾好了自己,让自己的生活过得比之前好了很多。第二,在照顾好自己的前提下,帮助了比自己要小的妹妹们。同时改变了两个小女孩的一生。
主持人:您曾经发起过对中国女性性侵数据的收集,这个数据库不是对外开放的发布项目。想在此问一下,从数据来看,有没有一些有哪些需要大家关注的,有哪些大家力所能及地可以做到的一些预防或帮助?
主持人:第一要相信小孩,因为这些事情它多发于在非常小的孩子身边,大多数都是亲人作案。在我们调查中,有很多的二次伤害主要是来自小孩在寻求长辈救助的时候,可能会构成二次伤害,因为她们没有办法得到很好的支持,她们可能会二次被质疑。
我们做数据库最大的目的是想要去量化受害者的伤害程度。因为大家过去只是觉得很痛苦或者很难过,但是没有多难过。所以我们当时花了一年的时间,用程序和人工对它进行分析到底有多痛苦。我们希望去量化它,以及对它未来人生的影响。所以我们做了这样的一个事情。怎么说还是很触目惊心的一些事情。我觉得从我们自己来说,更多的是去接支持这些人。
我觉得对于当事人来说,如果她愿意跟你说明,她对你是有信任也好,或者怎么样,她对你是有信任的。我觉得我们可能能做得不多,但起码要从情绪上去支持她,去接纳她,告诉她你是没有错的,我肯定是相信你说得对。我觉得是这样。